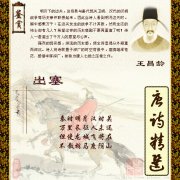|
从放牛娃到大学者 1946年,杨义出生于电白县南海镇万寿口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杨义祖上清贫,遗下的家当除了半屋子残破的八股古文的线装书外,其他一无所有。父亲杨校乙,敦厚睿智,从小佃田耕种,抽空自学,粗通文墨,练得一笔清秀毛笔字,是乡间小知识分子。杨义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贫穷又有书种的家庭。杨义从小受到文化熏陶,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些历史兴废古训故事,还没上学就会吟诗诵对,《千家诗》里的名诗名句他念得滚瓜烂熟。 后来解放初土改,外公分得一头牛,五六岁的杨义被拉去当牧童。在山坡上,人们常常听到杨义吟诵《千家诗》声。有时他会让牛自由吃草,跑到附近一所私塾隔窗听课,屋里学生未懂屋外杨义已会背诵。唯一的塾师见他有过人天资,连赞“神童也”,免费收为学生。那年杨义七岁。 1959年,杨义小学毕业,以全县前三名的成绩考入电白县第一中学。入学第一天,父亲教诲他说:“读爆书胆,呼风唤雨力无穷。”杨义牢记在心。中学几年,他以“读爆书胆”为目标,鞭策自己,遨游于茫茫书海中,他不甘心于课内书本,课余饥饿般阅读课外书,学校图书馆藏书,他借阅至少有三分之一,而那些文学书则几乎没有一本不留下他的指痕。天资加勤奋,让杨义文理兼优,理科尤其突出。在高考报考时,杨义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报考文科。校长忧他屈才,亲自找他谈话,说:“你考理工科,清华北大没问题,但考文科有所担心。”杨义沉思一下说:“我是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文科院校,回家还是有用的,到乡下至少可以当个小学教员。”其实那时文学已经开始扎根他的心里。后来他在某一场合引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人文精神,立国之本,英国人宁可失去最大殖民地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也许这才是他弃理从文的真正想法。杨义如愿考得高分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上大学时他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借书,不但读了不少文学名著,还对哲学、历史 产生了兴趣,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从中国哲学史到外国思想史,他一点点读下去。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他却自得其乐地遨游于书的世界,同窗们戏称他的生活方式是“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 ,杨义又放弃了新闻专业,报考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方向的研究生,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的研究生导师是鲁迅学生、著名学者唐弢。后来,他完成了24万字的硕士论文《鲁迅小说综论》,顺利获得中国第一批硕士学位(当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制度)。研究生毕业,杨义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全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工作的第一年春,他就提交要写150万字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科研计划。那可是一个“集体撰史”成为风气的时代,如此大的项目,需要组织几十个研究有素的学者,申请若干经费,召开不知多少次会议来研究切磋,才能完成。他一个赤手空拳的青年学人,独立撰述,有这份实力吗?完成这样的鸿篇巨著,并不是几个月一年的事情,他耐得住这份寂寞吗?在种种疑惑前面,这个项目既列不入国家的重点科研计划,就是在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也只能排行最后。杨义“十年磨一剑”,他花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三卷共150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十年间,他就是为了撰写这部书,阅读了两千多本原版书和大量文献资料, 做了过万张笔记卡片。当《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远隔万里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称赞这位年轻作者的“博学、细心”;第二卷出版后,他又来函预言“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将永垂不朽”;第三卷出齐后,他终于下了这样的判断:杨义是“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厚达2171页的“具有中国文学史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出世,便轰动整个汉学文坛,随后其与钱钟书名著《管锥篇》一道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并被列为高 校文科教材和现代文学研究生必读书,国外一些著名大学还将其作为教学基本参考书。因此,杨义在不惑之年就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 作为文学史家,杨义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界扛鼎之人”, 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古今汇通、中西兼容,文化气魄铺天盖地,为鲁迅之后少见的一位大师级的小说史家,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杨义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势如破竹地进军古代文学史,完成了另一个经典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接着《楚辞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论语还原》相继出版。研究领域从今到古,从文艺学到比较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从东方到西方,杨义显示出“谜一般的通才”。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9卷14册的《杨义文存》,一个国家级最权威的出版社为一个中年学者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术文集,这是没有先例的。一时,国内外很多媒体报刊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甚至有的竟占据了头版头条。杨义享誉海内外,他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汉城大学。他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讲演被该校的教授认为是“多年来请到该校讲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好的一位”,是“经典的讲演”。
|